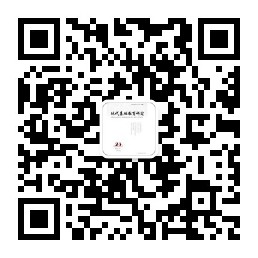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目录 【哲学研究】 孔子与“天人之辩” 崔宜明(5) 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 吾淳(17) 【公共管理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 ——可能性、必要性与基本取向 曾峻(27) 【心理学研究】 科学的含义与心理学的未来 高申春,祁晓杰(34) 职业决策困难:内涵、进路与发展趋势 王沛,左丹,过爱(41)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渊源论 冀运鲁,董乃斌(50) 中国文学伤春模式的起源 ——《诗经》中“女子善怀”之解析 严明,陈清云(58) 【都市文化与近代社会研究】 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以1949年前的上海为讨论中心 李培德(66) 无冕之王:近代上海的新闻记者 江文君(74) 从图像看晚清上海女性与城市空间 ——兼论图像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姚霏(81) 【外语研究】 汉英复句中副词性关联词语的逻辑关系比较 陆建非,原苏荣(88) 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 马莉(94)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世界环境与文学关系研究· 中国文学与环境危机 ——以阿城与姜戎为例 (美)唐丽园(100) 从广岛到福岛:核时代大江健三郎的反核历程 陈言(108) 【文艺学研究】 《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 杨矗(118) 多屏时代视频广告的叙事转向 何平华(129)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要目简介
孔子与“天人之辩” 崔宜明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孔子与“天人之辩”》指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天”总是与“人”一道被意识到,并且是相对于“人”而获得其概念的规定性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是一对核心的范畴,“天人关系”是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关系”,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反思和讨论就叫作“天人之辩”,“天人之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与“人”是如何勾连起来的。在先秦时代,儒家的创立者孔子和道家的创立者老子以“天人之辩”的核心问题——“天”与“人”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为中轴,建构起中国人观念中的世界图式。那么,在孔子那里“天”与“人”是如何勾连在一起的?在作者看来,在孔子而言,“天”、“人”关系可以表述为:其一,“天”赋予了人类生活世界的规律、原则和理想,是谓“天道”,并且通过特选的“人”赋予其“德”以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并且要求这个特选的“人”作为“天道”的担当者在人间实现“天道”,从而成为“天”、“人(类)”之中介和桥梁;其二,但是,“天”在何时、选择何人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的存在,以及这个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存在的“人”是否还同时具有“王”之位、从而在人间实现“天道”,那属于“天”的意志而不可知,是谓“天命”;其三,“道”之“在”,非“自在”,乃“自为”而“在”,作为“天道”的担当者,无论是具有“王”之位可以在人间实现“天道”者,还是仅仅作为“道”之“文”而彰显“天道”之存在者,其担当“天道”的方式都是“为”,行天道之“行”是“为”,显天道之“显”也是“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 吾淳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上撰文《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对于“天”的认识经历了从知识到思想,再从哲学到科学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三代或更早,夏商以后已经逐渐形成自然天人观,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已经成型。这些都构成了由知识而观念和思想的进程,并且为老子的哲学作了铺垫。老子在中国古代有关“天”的知识与观念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方面,老子从天道观中提炼概括出“道”的思想,由此将哲学从一般法则的水平提升到高度形上的水平。另一方面,老子又以对“道”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开启了中国古代天文史或科学史中的宇宙理论。之后,受老子思想的启发,战国时期有关宇宙问题的猜测开始普遍出现,秦汉之际这样一种猜测已经逐渐演变为天文学理论,到了汉魏时期终于形成丰富和完整的宇宙理论。无论是知识启迪思想、哲学启迪科学的进程,还是老子思想中哲学与科学的互证互启的关系,都是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完美经验例证。总之,这是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互为因果关系的一个经典范例。通过这个范例,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是如何在科学中汲取养分的,也可以了解哲学又是如何反哺科学的。通过这个范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包含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 曾俊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和分析过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职能、行政改革、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等概念和相关现象,对市民社会、官僚和官僚制度、中央集权和联邦制也有大量论述。类似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福利、公共舆论、公共经济等术语同样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论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抽象地建构和运用他们的理论,而是始终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具体问题,政府等上层建筑领域就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同样的一个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留下系统的关于政府管理的著述,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发现: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许多人眼中,《资本论》讨论的似乎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资本论》中包含着大量公共管理问题。在有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认识政府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在有关国家与政府起源、本质和功能的分析中可以认识政府的性质与角色,在有关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监督公共机关的机制和形式。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留下专门的公共管理著作,但在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存在理解公共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他们分析具体实际问题中可以提炼和概括有关公共管理问题的基本思想。当下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表现之一就是“失魂落魄”,即公共管理的价值、目标存在迷失。这或许首先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性质的理解有关。公共管理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应更多关注公共管理的“管理”层面,即其技术、工具和方法层面。公共管理的管理性议题理应关心,问题只是在于:公共管理学在走向实际的同时,会因太迷恋“技术”而迷失了“价值”,太关注“管理”而忘记了其前缀词“公共”。公共管理学面临着“魂归何处”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知识建构和价值塑造一是要求诸西方,二是要求诸传统,但更要求诸马恩。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代表着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高峰,他们在更高层次上且从崭新的路径指出了解放人的一整套思想和方法。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些思想和方法不仅作为不断为之努力的理想而具有意义,而且作为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而具有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指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历经9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克服西方理论和传统知识“横向移植”和“纵向移植”时可能遇到的障碍。第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可以找到中国公共管理核心理念的源头。但目前国内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研究总体视之,系统性和深入性还不够,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还没有发掘出来。并且对于文本的分析,还需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如何使分析尽可能接近原著者的思想。第二,如何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的特质。第三,如何系统地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管理思想。第四,如何处理好“六经”与“我”的关系。就马克思恩格斯公共管理思想而论,不同的人可以出于不同的需要进行解释,只要这种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本义,都应该被认可。总之,是问题决定了文本阐释的立场、重点和基本面,而非相反。基于这种考虑,可以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这样一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更加重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如何可能?它对公共管理的管理性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这些正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科学的含义与心理学的未来 高申春,祁晓杰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科学的含义与心理学的未来》指出:在心理学追求“科学”的历史中,关于“科学”是什么、心理学与“科学”是何关系、以及心理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实现为“科学”等问题,都不曾得到认真的追问和系统的思考。这个历史充分暴露了心理学的“科学”追求的盲目性。对现代人而言,“科学”这个概念的历史原型是自然科学。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质”或“身体”,与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或“心灵”,虽然它们本身在原则上是相互对峙、彼此对立的,但只有两者相加而成的和,才构成二元论世界图景的整体。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以非此即彼的排他方式专门针对其中的“物质”实体及其世界图景而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在与此相对应的意义上可以说,“心理学”恰恰是针对其中的“心灵”实体及其世界图景而建立起来、并在这个范围内有效的人类思维的历史成就。在这个背景中,“科学”和“心理学”必然构成人类思维所拥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体系,两者之间即使不说是彼此对立的,也必然是相互无关的,并共同构成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世界图景的整体。以这个分析框架为背景来看,“科学心理学”的观念是难以设想的;而且,在这个背景中,如果心理学一定要实现为“科学”,那么,它就必然要走向自我异化,从而暴露出“心理学”与“科学”之间的敌对性。心理学远离哲学的历史趋势决定了现代哲学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及其蕴涵的世界图景,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所不了解的。对于心理学这门特殊的“科学”来说,还必须真切地体验到“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及其差异性的洞察,才有可能超越“科学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历史及其产物所引起的种种困境,并跟进人类思维作为整体的历史进入现代哲学的理论视域,得以追求并实现类似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或“严格科学的心理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在理论上既获得关于它的历史的自我否定的勇气,又获得关于它的未来的自我确认的力量,在放弃它在历史上以“科学心理学”的形式所追求的、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背景的那种狭隘的科学观的同时,转而以现代哲学及其阐明的“科学”的范畴含义为参照,谋求实现它的理论思维方式的整体转换,进而有可能实现按照它的内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那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形态。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渊源论 冀运鲁,董乃斌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渊源论》,指出:小说叙事是中国文学叙事链条中最具综合性和最具主体意识的一环,小说文体的成长发展,是中国文学史叙事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无数小说的长足发展和积极加盟,中国文学史叙事传统就不完整,也不会生气勃勃,绵延不绝。不如放弃总想在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中分出谁主谁从、谁高谁低,乃至双方相搏、有你无我之类的“斗争”思路,而建立它们在不同阶段互有消长,成长发展有快有慢,但始终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和合”观念。以唐传奇为代表的文言小说,就和诗歌结有不解之缘,叙述中往往插入诗歌作品,诗成为小说叙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还是外在的形迹;叙事极富诗性,其想像之丰富超拔,情韵之雅致清丽,寄意之深刻悠远,这才是它内在的质素,而这些正是诗的本色。一切优秀的小说,无论是白话道出,还是文言写出,都是如此。清代文言小说不但出现复苏,而且再次形成高潮,达到新的高峰,文言、白话小说同时繁荣,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传统表现出走向成熟的征兆,沿其双轨直向其辉煌的终点奔驰。小说叙事乃是中国文学叙事最发达的一支,也是叙事成就最突出的一支。小说叙事在整个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不仅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叙事风范,而且还以其无限包容性,广泛继承和借鉴其他文学样式的叙事成就,成为古代叙事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最高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共生互补、相助相益的重要见证与典范。
环境危机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表现 唐丽园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中国文学与环境危机——以阿城与姜戎为例》认为,东亚的人类活动常常遵循的原则,今天可称为对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但环境问题依然存在。东亚文学的显著特征即歌颂自然之美,描绘人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现代甚至前现代东亚小说和诗歌都描绘人类破坏甚至毁灭自然。20世纪至21世纪的东亚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涉及环境恶化的作品非常多样。关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作品小部分持赞美态度,有的简单地进行描述,更多地则是加以谴责。这种的多样性一方面说明环境破坏持续存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学家的生态意识。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表现出了“环境含混”(ecoambiguity),即人与自然世界之间复杂、矛盾的互动关系。这种含混性无处不在。在中国,以阿城的《树王》(1985)和姜戎的《狼图腾》(2004)为例,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如何反映出两种重要的环境含混:一种为对自然的态度发生迅速变化,即同一个人/民族对自然的态度在敬畏、冷漠之间摇摆;另一种为“爱自然到死”,即人们似乎迷恋自然,却常常有意无意破坏甚至毁灭自然。
从广岛到福岛:大江健三郎的反核历程 陈言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从广岛到福岛:核时代大江健三郎的反核历程》指出,二战之后,日本依循美国冷战策略,将核电作为一种国家方案引进国内。尽管自从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受核轰炸迄今,日本历经四次重大核灾难,但是作为国家整体,日本始终没有从正面应对核问题。这样一个具有最直接意义上的“生存危机”的民族,在其文学领域对核问题的探讨却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蔚为壮观的“原爆文学”。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原爆文学”系谱中很独特的一位。他没有经历过核轰炸,却视广岛为自己的文学启蒙源点和文学根据地,除了创作以核问题为题材的随笔、小说之外,还参与编辑整理日本的“原爆文学”。他不断参加反核研讨会、发表反核演讲,致力于原爆受害者赔偿援助活动,多次向核轰炸遇难者捐款。广岛,是他突破文学表现的转折点,同时还是他践行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重要场域。而福岛,则是他背负着罪恶与苦难的广岛遗产辗转作战的另一个战场。在呼吁不要忘记二战的罪恶与苦难的同时,他企图将同胞从耽享物质的沉迷状态中唤醒,成为福岛核泄露事件之后最令人瞩目的反核斗士。他通过文学活动实现了自我救赎、成长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 杨矗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祝福〉的存在主义美学阐释》指出,人的存在论视角是在传统的政治批判视角、人性拷问视角、“叙事美学”研究视角之后,阐释和理解鲁迅小说《祝福》的一个新向度。《祝福》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现实主义之作,它要处理的问题已不是贫富对立、阶级矛盾或对传统的礼教批判,也不是简单的对“启蒙政治”的怀疑和反思,而是人的本体存在、人的生命意义或终极价值关怀问题。因此,说它是一部“存在主义”的象征之作更符合实际,“阶级论”、“礼教吃人论”、“人性拷问论”等都无法真正窥探到《祝福》的真意。《祝福》的象征是人的整体象征,而其象征的最大“支点”则是祥林嫂。祥林嫂是人的意义困境或存在论悖谬性的“哲学化身”,她的遭遇使人的意义的悖谬性被逼出了历史的地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人学思想谱系”后来被扭曲为与人的存在有悖的“道德人学”和“皇权政治人学”,《红楼梦》翻古开新创建了“贵情、尚真”的新人学,而鲁迅文学则是《红楼梦》新人学的真正后继者,《祝福》是这种新人学文学的新篇章。
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李培德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以1949年前的上海为讨论中心》提出,尝试通过口述史记录、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等不同资料,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上海人如何掌握上海城市生活的记忆和自我认同。他在分析中指出,记忆是个人的、主观的,由历史记忆而产生的认同当然可以被接受。不过,对于被创造出来的记忆或认同则必须加以识别。1990年代出现的上海“怀旧”热潮,无疑对我们的历史视野造成干扰,但毕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不难从中辨别的。上海的集体记忆,从今日的角度来看,姑勿论是否受到“被营造”的怀旧热潮或身份认同的重新建构过程影响。显然,1930年代和1949年前的上海,与1949年后的上海截然不同。就“上海人”的真正含义而言,并不简单拘束于籍贯,而是由工业化、移民社会、国际城市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地域人群”。因此,无论是在上海的广东人或是上海本地人的生活史,都应受到重视。毕竟,生活体验才是身份认同的源头。相反,在没有生活体验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去讲求“认同”。
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 马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通过从文化语用的视角透视法律语言翻译中所凸现的问题,进而唤起语言工作者及司法工作者在法律语言交流中的跨文化意识,使更多人关注法律语言中文化语用因素,从而推动法律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文章认为,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功能变体, 它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在法律语言的语际转换中,往往会有文化内涵的损失。英语国家法律文化中具体的法律特定概念、法律体系、法律词汇的文化语境、民族心理等都可能存在于语篇之外,因而会对处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读者造成意义真空,他们因缺乏应有的图式无法对文本获得连贯的理解,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尤其是在翻译充满文化负荷的法律语用修辞时,法律译员所面对的是两种法系和语言体系的双重挑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