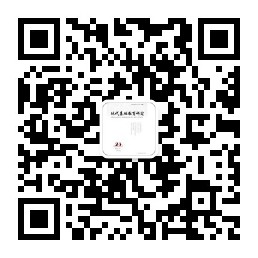《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推荐篇目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目录 【伦理学研究】 {enter newline}利益兼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 王正平,刘 玉(5) {enter newline}伦理的问题与儒学的智慧——兼谈汉学研究与哲学研究 杨国荣(16) {enter newline}【哲学与美学研究】 {enter newline}论阿奎那创世论的形而上学原则 吴广成(20) {enter newline}中西文化思想碰撞中的朱光潜美论 宛小平(27) {enter newline}【经济学研究】 {enter newline}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趋势权变相关套期保值研究 王周伟(34) {enter newline}非金融行业洗钱问题研究——以博彩业为例 李 刚(42) {enter newline}【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nter newline}庾信山水诗的世俗化及其意义和影响 赵沛霖(55) {enter newline}【跨学科研究】 {enter newline}唐代明经科试的体系、方式及其地位变化 俞 钢(65) {enter newline}潘光旦译注《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解读 王 健(73) {enter newline}【非洲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舒运国 {enter newline}中国对非援助:历史、理论和特点 舒运国(83) {enter newline}中非减贫发展理念的比较与分析 安春英(90) {enter newline}中国对北非国家投资现状、动因及策略选择 张小峰(97) {enter newline}【中国现代文化研究】 {enter newline}重新解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当代意义 邵盈午(104) {enter newline}自由主义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论证 胡明贵(112) {enter newline}【影视文化研究】 {enter newline}视觉媒介的表述底线 贾磊磊(124) {enter newline}从创意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与问题 汪献平(130) {enter newline}《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推荐 利益兼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 王正平,刘 玉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利益关系日呈复杂化。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现实,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原则。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在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解和宣传中存在着“左”的倾向。强调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中心,一方面避免了极端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侵害,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把个人始终放在从属地位,容易忽视人民群众个人的正当利益和当下的现实利益需求,压抑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绝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而不断提升。必须变革与之利益格局变化不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建立适当的道德原则,来合理、有效地引导当下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传统的“集体至上”道德原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无法为人们对正当的个人利益追求提供伦理道德上的支持,因而难以为广大公众自觉自愿地普遍接受。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至上”道德原则,由于不能维护社会集体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势必严重损害社会集体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的实现,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更不利于人们思想道德境界的逐步提升。真正有效的社会道德建设,必须一切从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寻求和建立既能顺应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变化的客观要求,又能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相契合的道德原则。利益兼顾就是这样的一种道德原则,它要求任何利益主体都不能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要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倡义利兼顾、互利共赢,提高和增进社会综合利益。利益兼顾原则追求的是合理、有效和均衡地分配和调节利益,提倡义利兼顾、公私兼顾、他我两利。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上,坚持把三者利益的和谐一致、统筹兼顾作为利益出发点和利益基准点。把利益兼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应当遵循的一项根本道德原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符合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又符合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利益兼顾原则能合理有效地引导当下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思想,协调重大利益关系,规约社会行为,醇化社会风气,实现社会和谐。 {enter newline}汉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存在内在的相关性 杨国荣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撰写《伦理的问题与儒学的智慧》一文中,提出传统智慧的反省与今天的理论思考之间存在内在的相关性,两者的彼此沟通,对汉学研究和广义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经常面临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的对峙。道德相对主义往往注重具体情景、个体选择、个体判断,等等;道德绝对主义则每每强调普遍原则,或将普遍原则绝对化。如何克服两者的对峙?传统儒学的有关思考,似乎也可以提供某些启示。事实上,早期儒学已以不同的方式,面临并探索相关问题。这一点,从发端于孔子的关于“经”和“权”关系的思考中,便不难注意到。孔子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一方面,他对“仁”这样一些普遍价值原则的绝对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便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一类原则的运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具体的情景,“无适也,无莫也”侧重的即是这一方面。这种观念在后来进一步展开为关于“经”和“权”的关系的具体讨论。“经”所侧重的是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权”则涉及一般原则的变通,后者蕴含着对原则相对性的确认。从总体上看,儒家不赞同“经”和“权”的绝对相分,而倾向于肯定两者的沟通,从孟子到荀子,以及尔后的儒学,都表现了这一趋向。“经”和“权”的这种沟通,既不同于道德绝对主义,也有别于道德相对主义,这种观念对我们今天适当地理解道德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同样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 {enter newline}重新解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当代意义 邵盈午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腾实飞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距今已逾80年;它在历史上的存在虽仅4年,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从表面上看,其主因似乎是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的相继殂谢,不复为继。 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国学研究院的特殊定位与所面临的时代风潮的冲突、传统学术在近代学科体制转型过程中所遭逢的两难困境,以及传统书院式的通才培养与现代教育对专才的倚重之间无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恐怕才是其自我终结的真正原因。国学研究院在定位上大力标举其自外于学科体制的立场,较之北大等研究所将国学纳入学科系统的做法,确实更能体现传统学术的不重分科的特质;但国学研究院的停办,也正是由此所致。事实上,国学研究院取消后,清华的人文学科并未中断,经由“四大导师”所创发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已然在清华得以确立,一种理想的宽松、自由、和谐、平等的大学学术研究氛围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光荣传统已然形成,并奠定了学术权威进行学术管理的框架。同时,四大导师成功的学术实践也积累了他们的权威资源,清华大学不仅成为当时的国学研究中心和学术重镇,更重要的是,清华学人以自身的实践开拓出一条实现的道路——这在今天已然习焉不察的一切,若细迹其由来,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些与我们紧密关联的事物,都有着一条向后的通向源头的道路——正是在那因遥远而视野虚渺的地方,才有先贤们最扎实、最坚执的脚迹。今天,重新“回首沧桑路”,虽然此举未必能够对现代的学术运行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提供直接的应对效用,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人文境界的象征,它至少可以为当代学人和现行学术体制提供一种反思,一种参照,一种文化自省,一种价值理念,乃至一种精神范式与人格自律。 “五四”反传统无可厚非 胡明贵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撰写《自由主义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论证》一文中提出:“五四”反传统适应时代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诉求,从本质上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因而无可厚非。从“五四”反传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五四”反传统不是什么“全盘反传统”,而是有选择地反对那些毒害中国人思想、戕害中国人性灵、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专制思想以及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依据并起着教化作用的儒教。2.“五四”反传统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启蒙,就是要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科学大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蒙昧主义,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共和等新思潮,启示国民为此而做出不懈努力。这些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可见,“五四”反传统是和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心声是一致的,是符合社会与历史进步要求的。它的反传统以后形成的新传统——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它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它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认真态度,它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积极追求,都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及民主进程还远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要时刻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复兴民族文化传统的旗号复辟一些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过,曾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许多不幸和沉重灾难的“传统”。我们尤其要反对那些假借现代、后现代所谓颠覆、所谓解构这些新名词、新花样的“新儒们”思潮混乱视听,混淆是非,破坏干扰我们正在形成中但还非常脆弱的一些优秀新传统的成长。 {enter newline} |
| |